祛魅后的西部写作
——评马文秀诗集《照进彼此》
赵俊
对于中国西部诗人而言,昌耀似乎永远是一座高峰。所有西部的写作者都绕不开昌耀这个话题——甚至于,在某种意义上而言,他已成为一个母题。正像十九世纪下半叶到二十世纪初的法国一样,人们永远无法逃离象征主义的窠臼。于是,波德莱尔就成为了一座形而上的阿尔卑斯山,人们只能在山脚下仰望。可以说,波德莱尔和象征主义,已经成为一种法国的诗歌传统。而中国当代西部写作的传统无疑是昌耀,他构成的诗歌镜像正在映照几乎每个西部的诗歌写作者。
昌耀长期生活在西宁。是以,西宁成为了西部诗歌的“圆心”。对于西宁的诗人来说,昌耀的“圆心力影响”显然更加突出。的确,马文秀对昌耀也有着不一样的情感。可以说,比如在《哈拉库图》一诗中,就有着对昌耀的一种致敬,这首诗的最后一段是这样的:
我与诗人远村迷了路
绕着村子寻找诗人的影子
一圈接着一圈,走进
诗意的迷宫
却又像是诗人昌耀
变着戏法在挽留我们
但无论如何,作为一种现代写作,我们必须勇敢地祛魅。作为一种语言的创造,诗歌永远在面对一个永恒的仇敌——陈词滥调。有时候,陈词滥调比语言本身更顽强,它时时刻刻都在对战着创造的动力,并且常常能够取得领先优势。在舒适区写作是安全的,它并不需要你作出太多痛苦的抉择。有时候,这甚至是诗歌写作中的巴甫洛夫反应。
第一次见马文秀的时候,是2015年在西宁她的大学里。她娇小、羸弱的身躯在倒春寒中瑟瑟发抖。在一棵还未发芽的、光秃秃的枣树下,她静静地站立,仿佛一只还未吃饱食物的雏鸟。这也是我对那时她写作的一种观感。那时候,她的诗歌写作多少是青涩的。如果非要加一个定义的话,无疑是“诗歌的学徒期”。
在一个名为“女诗人”的公众号上,我读到一首她的诗——《不曾被遗忘的瞬间》。在这首诗里,她所抒写的是戈壁生活。在早期的写作中,她动用的所有抒情的力量。那时候,她的阅读视野似乎还不够广阔,但她仍然凭借着一种女性特有的敏锐写出了西部的独特风貌,为戈壁涂上了“马文秀色”,尤其是最后三段,已经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声音:
忧伤的白犀犀牛
寒夜的篝火,荒原的曙光
这里,不再是我望而却步的寒酷荒寂的绝境之地
冬日,充斥在厌铁的心情里
折叠的憔悴,静谧的忧伤
再不被遗忘的瞬息守望着
在颤动双峰的金骆驼,涉足我孤独的草原时
听,羊群咀嚼的声音
十个手指的环抱,在骆驼之日中守候
布罗茨基曾说过:“保持语言的精准。像对待银行账户那样尝试创建和对待你的词汇,时刻专注并增加你的积蓄。这样做的目的不是促进卧室口才、职业成功或成为交际场合的雄辩家,而是为了尽可能充分、精准地表达自己,保持自身的平衡。”作为有独特经验的诗歌写作,你需要诚实地面对语言的问题。无疑,马文秀在这部诗集中已经在自觉地面对这些问题。可以说,那时候马文秀的写作还停留在一种将抒情转化为词语的阶段,并没有洞悉布罗茨基的箴言。
然而就在这不久之后,马文秀作出了一个重大的选择——离开西宁,离开她生活了二十几年的西部语境,到京城去,去拓宽自己的人生,也让自己的诗歌写作更趋向于一种现代文本。
其实,昌耀之所以能够成为昌耀,也和他并非来自西部有一种内在的联系。如果昌耀永远住在常德那个商业街,他就永远是那个王昌耀了。“昌耀于1936年6月27日出生于湖南常德城关大西门内育婴街17号,而其家族的老宅,则在常德下辖的桃源县三阳镇王家坪村。此时,昌耀的祖父王明皆作为三阳地区有名的地主,整个的王家坪村几乎就是王氏家族的产业之一 。”这是燎原在《昌耀评传》中对昌耀出生的描述,这显然和读者想象中的昌耀大相径庭。
在北京,马文秀需要面对现代生活带来的许多困境。毫无疑问,她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北漂。甚至于,因为工作原因,她需要去四处行走。在诗集的后记中,马文秀这样写道:“我是一个向往远方、喜欢行走的写作者。我认为,万物皆是路标,诗意的远方为我打开了思维的视角, 生活的历练为我的诗歌写作注入了活力。”
这种行走,无疑给马文秀的“西部祛魅”提供了一种天然的养分。作为中国最杰出的诗人,杜甫有一种强大的能力——走到哪里就写到哪里。无疑,这是对沃尔科特“忠于方圆三十英里写作”的东方式反击。马文秀用自己的实践,在延续着这种诗歌传统。
在《今夜住树屋》这首诗中。马文秀向读者展示了浙南山区的一种地理风貌,也用这样的句子表达了她当时的雀跃:
生长在屋子里的树
抖擞精神,用绿叶证明价值
交错的枝干伸出墙外
采撷星空的灿美赠予我
让我心隐于谷
打捞藏在山水间的诗句
这样走到哪写到哪的写作方式,无疑为马文秀的诗歌写作增强了她独特的视角。“我感受”变成了“我看见”,这是一个女性诗人走向成熟的的必经之路。由于女性天然的抒情特质,往往会疏忽掉一些沿途的描摹。过度的抒情其实削减了诗意,而这种观看是一味良药,它将马文秀早期过于关注自我感知的自怨自艾中拯救出来,带来了全新的生命体验。这种体验,是现代写作的有效路径。
同时,离开青海后,再回望故乡,为她的诗歌提供了一种新的经验。这也是一种昌耀离开家乡后的一种致敬和互文。在这种诗学实践中,也是对西部诗歌写作的一种祛魅。固然海德格尔说诗人的天职是还乡,然而,现代意义上的故乡又是一种飘忽不定的概念。它时时刻刻都在发生着变化,不容你倔强的说辞强行将它挽留。比如这首短诗《雪白的鸽子》,就是对故乡生活的一种独白:
深情的对唱,让雪白的鸽子
在彼此的眼中找到了天空
从那座山飞往了这座山
飞行的轨迹是一朵玫瑰的形状
开在了过去也开在了未来
只有此时,我们或许意识到
曾经离去的背影过于锋利
划开了夜色一道口
多年来,我们带着故乡的星辰
在漆黑中走向远方
却不知道彼此遥望时
折射出的光芒,比自身还耀眼
在这首诗里,固然有很多山的意象,但在诗中已经出现了“玫瑰的形状”。在我有限的阅读里,西部诗人非常喜欢运用“雪莲花”这个形象(西部有本文学杂志都名叫《雪莲》)。而玫瑰作为主角,我第一次看见是在昌耀的遗作——《一十一枝红玫瑰》。这是写给他生前爱人卢文丽的——“一位滨海女子飞往北漠看望一位垂死的长者,临别将一束火红的玫瑰赠给这位不幸的朋友。”因为带了江南的元素,昌耀在诗里一下子送上了一十一朵玫瑰花。这似乎比他一生所动用的玫瑰还要多。而在这现代的演化中,在马文秀的诗里,玫瑰是一道飞行的轨迹。虽然,“曾经离去的背影过于锋利,划开了夜色一道口。”这让我想起海子《最后一夜和第一日的献诗》中的诗句:“黑夜是神的伤口,你是我的伤口,羊群和花朵也是岩石的伤口。”在这种忧伤的气氛中,幸亏,马文秀笔锋一转:“多年来,我们带着故乡的星辰。在漆黑中走向远方,却不知道彼此遥望时,折射出的光芒,比自身还耀眼。”这是一种忧伤中萃取的豁达,它也指向现代文明的一种终极关怀——虽然现代性危机时时刻刻都在爆发,但只要人类能够正视自身的问题,终将完成一次文明的自我救赎。因为,这文明比自身还耀眼。在这首诗里,马文秀既是在写故乡,也是在讲一种自身对待世界万事万物的态度,这是一种超越一种青春期的写作,虽然还没有形成“晚期风格”,但这肯定是写作中的跨跃性行进。
对艺术的探究,让她能够超越经验,得到一种超越的体验。她长期对梵·高的迷恋,让她写了很多关于美术的诗作。景凯旋在《走出叙拉古》一文中这样写道:“从观念史的角度看,轴心文明是人类的第一次观念突破,其标志就是一个具有超验维度的哲学或宗教出现,由此奠定了文明的普遍价值,并以超验、永恒和绝对的道德善作为人类活动的目的。”无疑,这部分的写作,确实为马文秀走向一种现代性的写作提供了新的可能。
在组诗《与凡·高相遇》中,马文秀解读了他的自画像、割耳之谜和数幅油画。为此,她写下了这样的诗句:
哦!英俊的男子— 凡·高
跋涉在体内的色彩,喷涌而至
疯狂的白羊在画纸上奔腾
陌生、惊愕,目光急速
搜寻熟悉的印记
来不及想象那肆意而茂密的绿意
自画像早已挂满墙壁
无疑,在马文秀的这组作品中,我看到她对世界的认知早已超越了那雪域高原。在旁人惯常的理解中,雪域高原是广阔的代名词。然而,在常年对广阔的误解中,雪域高原变得细长、狭小,反而成为了一种偏执。马文秀,对世界真正的认知,始于破除那些印象中的广阔。在对这位天才画家的解读之诗中,一个真正广阔的女性诗人跃然于纸上。从此,她不仅完成了西部诗歌中关于诗歌的“祛魅”,也完成了自身的“祛魅”。
“祛魅”一词是马克思·韦伯思想中最常被提及的概念之一。韦伯认为,“世界祛除巫魅”是一个社会理性化的重要标志,这意味着曾经崇高的价值逐步隐退。比如,在原始的“图腾时代”,自然往往被赋予了神话的象征,现代人却可以运用高度发达的理性以及先进的技术手段揭开自然神秘的面纱,将其转化为可以利用的资源。在马文秀这里,她理性的声音就是将现代诗歌的写作方式扛在肩上,而不再背负为西部或者“部落”写作的十字架。在完成前一本长诗集《老街口》之后,她在艺术上尝试了各种追求。如果说,《老街口》还有着某种单一性的话,诗集《照进彼此》已经丰富了她的诗学实践。诚如点睛诗作《照进彼此》所言,它已经成为一束光:
或许,你我本是一束光
向下抓紧泥土
向上迎接太阳
能照进彼此
说明本身留有缝隙
这种缝隙是一种等待
足够一束光进入,温暖彼此。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作为一个少数民族诗人,马文秀其实比我们跟注重音乐性在诗歌中的运用。在越来越散文化的当下写作中,这应该是一个异类。但这并不影响她在往现代性方面的努力。有时候,她也在追求音乐性方面稍微有所放松,为了配合现代词汇和意识在她的诗歌里潜行。这种自然是必要的。不过,我想说的是,对于这方面的追求,对于包括我在哪的汉语诗人而言确实有所松懈。向这种带有异域甚至异质的女性诗人学习音乐性,是我们抵达现代汉语之泉的踏脚石。
— END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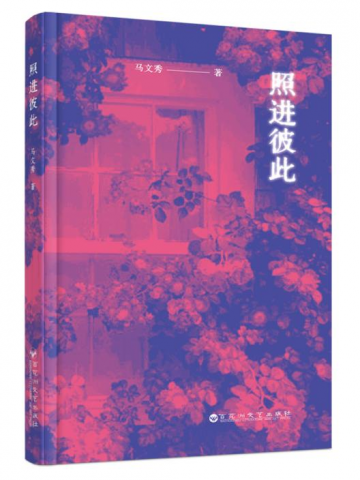
 津公网安备 12011302120484号
津公网安备 12011302120484号